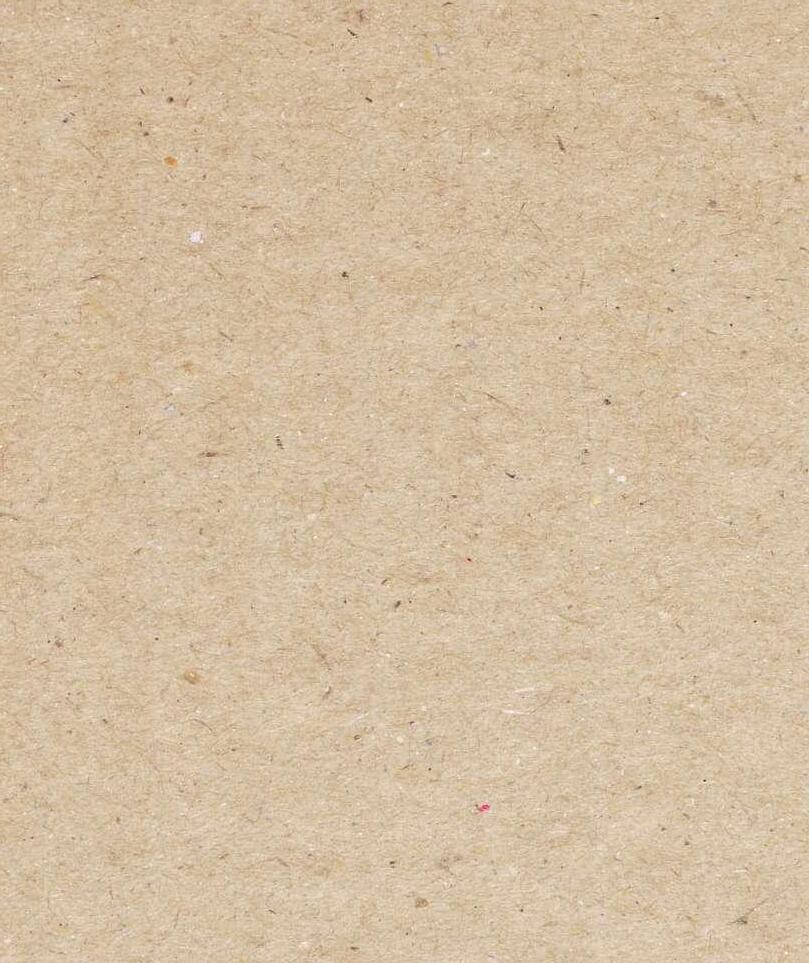城视

city eye
Complimentary 赠阅 32
报
著作权所有, 本社区报图文非经同意 不得转载或复制。
Published by 乔治市文创中心
GT Creativity Centre 19, Tingkat Besi 2, Green Lane, 11600 Penang, Malaysia

Penang City Eye 城视报 召集人 黄伟益 出版单位 乔治市文创中心 策划统筹 黑土设计所 出版总监 庄家源 主编 张丽珠 编辑 徐秋雁 采访撰文 徐秋雁 | 赵慈宇 摄影 Fox Foo 设计 曾伊霓

Contact +6019 472 6525 cityeyepg@gmail.com
Special Thanks 亚洲文件夹集团主席拿督林顺发 赞助本刊全部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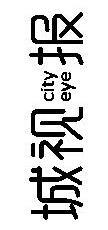
Printed by Asia File Products Sdn Bhd 16, Kawasan Perindustrian Bayan Lepas, Phase IV, MK12, Bayan Lepas, 11900 Penang, Malaysia
pg. 4~7
关注乔治市的生活与文化
城视报创刊于2014年5月,每三个月出版,
从2019年开始,进阶为双月刊,每期发行一万份。
是一份由写作人、设计师及摄影师等人共同编制的 社区画报。可在乔治市一带的咖啡馆、餐厅、书店、 民宿、主题馆、人文空间等地方免费索取。
撰文 | 赵慈宇、 徐秋雁 特约摄影 | Fox Foo
pg. 8~17
Geor g e Town Lifest y le and Culture
pg. 18~22
公园,我们回头再看情深意重的社尾人 社尾事,当中承先启后的部分,值得深思 和珍惜。
早在1983年,社尾万山已被列入光
大第5期发展计划范围。直到90年代,各
马福建及潮州人多数将菜市 叫做“万山”,它取自马来语
注:此主题为“社尾万山万象”社区记录计划 部分记录。本社区记录计划由槟州旅游与创
种规模的超级市场开始普及,社尾万山 渐渐失去槟城最大批发市场的地位。其 后的各种事件,让社尾万山频频上新闻
意经济行政办公室支持,乔治市世界遗产机 构主办,《城视报》协办。

版面。2004年12月16日早晨,挖掘机抵 达社尾万山,将它推平了。
Bangsal,除了是住人的大棚屋、草棚, 也有售卖东西的摊位之义。槟城就有两 个万山代表,一个是吉灵万山,另一个则 是已消逝的社尾万山。上个世纪中期,社 尾万山是实实在在的批发市场,有货品
光阴荏苒,时移势易,“社尾”两个
字现今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号,一提到 “社尾”,总能勾起中老生代无限美好记 忆。17年过去了,走在绿意悠然的社尾
齐全的杂货店、干货店,以及24小时运 行的食肆。这个万山,是市井人民采购日
常用品的巴刹,是夜猫子寻味的好去处, 亦是中老生代的生活记忆。
北
02 03 故事
尾万山考古公园集遗迹、绿 化和休闲三种元素,2019年
刚建成时一度成为年轻人们的打卡 热点。公园内由港仔墘运河改造的鱼
池,如今已是乔治市内的一道风景, 询问不同年龄层的社尾人对于
这条河的印象,他们却会给出两种截 然相反的形象:老年人们会说,小时
候这里清澈得可以在里面游泳;中年 人的记忆中,这里却是浑浊而腐臭的 大沟渠。然而,这条河所存在的时间 与形象的变化,可在这些人们的记忆


以外推前一些,追溯到更早——200 社尾万山曾经非常兴盛,是无数
草根人民奋斗发家的起点。而社尾人 群的聚集,还得从这条河说起。
运河进化史
从护城河、沟渠到鱼池
确切来说,人们惯称的港仔墘运河(Canal)其实 是一条水道(Ditch)。

港仔墘运河原来是一条小河,1804年拿破仑战
争爆发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用了3年将小河加深加长,
成为保护行政中心的护城河。战争结束后,运河变身
贸易水道,是当时海上船运与乔治市内陆的重要接 口。同时,港仔墘运河也是一条城郊边界线,将当时 的乔治市内外区隔开来。连接城郊的安顺桥东北边是 乔治市之末社尾,西南边则是郊外“过港仔”(Bridge Street,现已更名为崔耀才路)。 随着陆上运输逐渐方便发达,运河也就转型为水
道,成为乔治市的排水沟。英殖民政府在1880至1890

年间提升运河的结构,将运河缩小并装置闸门;并从 英国德比和伦敦进口铸铁框架,建设港仔墘市场,也
就是当今俗称的社尾万山。社尾万山乘着这条运河周 边交易的繁荣而建起,成长为北马最大的批发市场。
在高峰时期周边曾设有巴士总站、学校、购物区和游 乐园。
这些年来的城市发展下,全长11.7公里的运河许 多部分已被柏油路掩盖。社尾万山那段220米依然曝 露在外的运河,也因长年累月被投入各类垃圾而发出 阵阵腐臭味。
故事
上图|老社尾时代,运河两边 都是营业的商家。(陈耀威提 供,摄于1999年)
下图|社尾公园这一段露天运 河经过净化,摇身一变清澈的 鱼池。
04 05
迹,世遗机构也在社尾万山展开“当代考古计划”,从
港仔墘运河的淤泥中筛出了1万5000余件当代文物。 它们横跨两个世纪,以1960年代后社尾万山的生活物


件为主,是这些年来社尾商业形态、庶民生活的缩影。

社尾万山考古公园 在世遗机构的管理和策划下,运河盆地和警察营 房双双被列为遗迹,计划将成为公园内的考古点开放 给民众参观,作教育用途。社尾公园范围内的社尾万 山旧址、运河、水闸遗迹、警察局遗迹和安顺桥旧址, 包括运河出土的物品和尚在世的老社尾人,都是民众 近距离实地认识本土历史的活对象;公园种植了绿植 并设有游乐设施,也是男女老少们不必消费便能享有 的休憩玩乐空间。这个城市公园,对于槟城人来说,可 以是娱乐的、休闲的,也可以是学习的多功能场所。 左上图|社尾公园的新颖游乐设施,摩登设计和 周边老城社区新旧融合,并不违和。 左下图|社尾万山拆除后,露天运河的全貌终于 被看清,原本全长11.7公里的运河随着城市发 展,许多部分已地下化。(陈耀威提供,摄于 2005年) 右图|经过净化的露天运河,池里鱼儿成了社尾 公园最美的风景。
遗迹再发现
社尾万山丢空了10年后,槟州政府在2015年启 动“春回社尾”计划,将社尾万山旧址打造成城市公 园。工程的第一阶段便是建造一条港仔墘运河绕道, 并将社尾区域内的露天运河净化改造成鱼塘。绕道工 程进行到11月,工程队却在运河边发掘出历史不曾记 载的不明结构。2016年经理科大学全球考古研究中心 挖掘评估后,才确认那是老港仔墘运河的盆地(Canal Basin)以及超过百年历史的泄水闸门。这也是马来西 亚乃至东南亚首次出土的运河水闸。槟州发展机构随
即委任乔治市世界遗产机构(GTWHI)管理社尾遗址, 以确保该地受到妥善的保护。
考古队根据19世纪末绘制的凯利地图(Kelly
Maps)在水闸出土处周边继续搜索,紧接着发现了历 史超过200年的警察营房。除了修复保留几处建筑遗
有早市,到了下午就陆续收档。说到“社尾”的名字来源,以前在 中国大家习惯性称呼一个小区为“社里”,而在社里后段的地区 就叫做“社尾”。那时候社区里几乎是同姓氏的人住在一起,当中 住着潮州人、客家人等等。
他回忆道,于50年代初期,当时住在七条路的老槟城其实不

太喜欢去社尾。因为那时候来了很多从中国来的“新客”,新客们
口中说惠安方言,与本地人语言互不相通,造成不少困扰。 70、80年代可说是社尾万山最巅峰的时期,当时没有太多 商店和超市,人们多数到巴刹采购年货。在那个年代,许多巴刹
在农历新年之前都会通宵营业,因为打工族都是新年前几天才 领红包,才能办年货。当时最热闹的新年巴刹当属吉灵万山和社 尾万山。此外,每年中元节普渡庆典也是社尾人流沸腾的节点, 上有歌台、潮州戏班和布袋戏等,下有戏棚脚各种美食,不过此 盛景也已成为老槟城的集体回忆。
谢清祥亦是槟城福建话研究者,他表示旧时的槟城福建话 口音跟现在截然不同,像是某些祭文中的福建注音,现在的人即 使照着念,也无法参透其中的意思。他感叹,从旧时代一路走来, 很多专属于那时候的特殊印记,来到今天已变得鲜人听闻。 70、80年代可说是社尾万山最 巅峰的时期,当时没有太多商 店和超市,人们多数到巴刹采 购年货。在那个年代,许多巴 刹在农历新年之前都会通宵营 业,因为打工族都是新年前几 天才领红包,才能办年货。

老槟城谢清祥 七八十年代的社尾最热闹
78岁老槟城谢清祥的曾祖父10多岁从中国的福建漳州南
简介|谢清祥生于1943年的日 治时期,精通英文与闽南话, 目前任职槟城龙山堂邱公司旅 游营业主任,积极推广槟城旅 游文化。他也是槟城福建话研 究者,著作《槟城福建话》记 录了当年从中国福建漳州南来 的祖先们使用着的福建古话。
下之后,谢家就在槟城落地生根。对槟城古人旧事记忆犹新的谢 清祥,过去一直是本地写作人杜忠全的访问对象,是《老槟城·老 生活》主要口述人,细述许多属于老槟城的老故事。
追溯回社尾的历史,其实早在约1929至1930年间开始有了 社尾万山,当时还是槟城最早的菜市场。据悉早期的社尾万山只
06 07 故事
社尾孕育了许多老商号,谱写了一篇篇南来移民的创业 发家史。但紧随着社尾万山被拆除,许多小食摊、商店也
老
连同消逝在历史中。庆幸的是,还是有些商贩坚韧地存活下来。

除了有中老生代最爱的社尾经济饭古早味、一景包点等食肆,还
有老翁茶,泉隆等等老商号分享他们的旧社尾生活。

142社尾经济饭
73, Jalan Magazine, George Town,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每天上菜近50道菜 色,有些是社尾招牌 菜,也有后来添加的 新菜色。
社尾特色炸猪扒
自父亲过世后,这家店则由陈世音和陈世龙两
姐弟全力掌厨。他表示社尾经济饭一定会有咖喱魔鬼
鱼、咖喱豆卜、炸猪扒(俗称bak-steak)等招牌菜,尤
其社尾炸猪扒是其他经济饭档找不着的好滋味。初期
社尾经济饭档是用玻璃盘装饭,后来为了方便改用塑 料盘子,他还记得他们专用蓝色盘子。
2019年社尾万山考古公园开幕,陈世龙阔别多
年回到熟悉的地方,竟流下男儿泪。那排空置多年的
22家社尾老屋,据说相关单位有打算将老屋重建商
店,让从前的小贩回来经营,但听说了多年,这方案似 乎遥遥无期。“如果可以,我希望可以回到社尾,继续
经营我们的杂饭档,这也是我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
社尾是个不夜城,从早到晚都有人卖饭、买饭,半夜放
工归家的人不怕没饭吃。当时社尾共有142个注册档
口,他们家经济饭就是最后一号。里面共有7家经济
饭,有早市和晚市之分,轮流为不同时段工作的中阶 层人士提供热腾腾的饭菜。
目前仍在经营的经济饭档仅剩4家,一家入驻五
条路珍珠大厦,两家搬迁至七条路附近,他们则搬到
距离社尾最近的头条路。第4代传人陈世龙表示父亲
决定在头条路重新营业时,由于新址停车位少,加上
乔治市人口流失,新店前景不被身边人看好。不过这
十几年来父亲经营有道,142经济饭也越做越兴旺。
08 09 故事
济饭。
陈世龙三姐弟陈世音(左起),陈 世娇,陈世龙与姑姑(右一)以及 咖啡店老板林莲风合力经营142经
加兴经济饭
118, Kompleks Pulau Mutiara, Gat Lebuh Macallum,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最为集中的经济饭档
加兴经济饭主人陈开裕欣然接 受搬入大厦的决定,即便生意 下降也守住岗位。
“以前经济饭档集中在同个地方,不像现在到处 都是经济饭档。所以讲到社尾,人家的印象就是吃饭, 去到那边就一定有饭吃。”
他还提到,“经济饭”这名字与社尾息息相关。这 说法虽无从考证,但他那年代的经济饭售价确实非
常经济实惠(干鱼片6毛钱、菜2毛钱),再加上当时只 有社尾区经济饭档最为集中,且全天候服务,所以相 信““经济饭”之名由此而生。
珍珠大厦里的咖啡店与食
摊,有一部分是从社尾万山 迁移至此,继续服务街坊。
陈开裕于90年代接手祖传“加兴经济饭”,卖饭至今将

近30年。当年他们家的档口就在一景包点隔壁。社尾
拆迁后,他和其他商家齐齐入驻珍珠大厦。搬迁至大 厦的这些年,饭档的顾客少了大半,来光顾的大多是 五条路居民和从前的老顾客。
当年,到巴刹采购的人、周边公司的上班族等,到
社尾吃经济饭的人可不少。社尾万山经济饭是全天候 轮流营业,加兴经济饭从下午6点营业至12点,之后由
别家经济饭接班。
社尾兴饭店

274, Jalan C.Y. Choy, George Town,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上图|招牌放上“社尾”两字, 方便老主顾寻味。
下图|郭廷雄与母亲冯秀琼继承 祖辈饭档,喂饱了几代人。
夜归者的宵夜之选
郭廷雄表示当时社尾经济饭多是轮流卖饭,而他 们家是全天卖饭,外公负责早市,母亲则负责晚市,外
公每天早上7点多就得到社尾准备菜肴,早上九点开 始卖饭,直到下午3、4点,再由母亲接班卖到凌晨3点。
以前的人生活朴素,最大的娱乐就是看电影,尤
其星期六晚上常常可以看到老少携幼一起看半夜场 电影,一买就是一整排的座位,十分壮观。当时社尾附
近有东方戏院、卡拉ok和夜总会,即使凌晨两三点仍 不乏人潮,社尾经济饭也成了最受欢迎的宵夜。
43岁郭廷雄是社尾兴饭店第四代传人,他们几代人原
以“汉香饭店”在社尾卖饭几十年,搬离社尾后,他们
便以郭廷雄的父亲郭志兴名字为店名,“社尾兴饭店”
就此驻扎七条路17个年头。店后面就是七条路巴刹, 采买食材可说是十分方便。
店里墙上有副黑白老照片,照片里郭廷雄的外公
冯吉宁当时只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在饭档负责装 饭,曾外祖母和曾外祖父则负责掌厨,至今经营超过
百年。郭廷雄听长辈说,当时曾外祖母是挑着扁担走 遍街巷卖饭,进而在社尾万山租下小档口,不过“汉香
饭店”这名字的由来就无从得知。
10 11 故事
社尾兴饭店离开社尾搬 到新址后,也累积了另 一班忠实顾客。
玉展饭店

上图|陈玉展的“bungalow经济 饭”傍晚才开档,菜色丰富鲜
社尾经济饭档一定会有咖 喱魔鬼鱼这道招牌菜,是 老中生代留恋的好滋味。
讨饭吃亦相赠
这家经济饭档于二战前已开始营业,传至陈玉展已是
第三代,在社尾万山时以档号133和134为名,自1989 年从母亲手上接过经济饭档,老板就以自己的名字命 名为“玉展饭店”。这位于七条路巴刹对面的饭档,因
玉展饭店搬离社尾后,从头条路的“美凤茶室”辗
转搬到七条路这家排屋,许多社尾老主顾寻味而来, 甚至是政商名人亦前来光顾,偶尔有流浪汉前来讨 食,他也会慷慨相赠。后来旧社尾粥档老板余振财也 入驻店面,一饭一粥同在屋檐下,无论是早上或傍晚 总有人潮。可惜粥档在几年前因后继无人结业。
艳,让人们好想赶紧吃晚餐。
设在排屋式的店铺,附近街坊都称它为“bungalow经 济饭”。玉展饭店的经济饭是晚上飘香,傍晚时段开档 至晚上。 原本从事五金行业的陈玉展,中途转行接手母
亲的饭档,他笑笑说:“男孩子就是要向外闯,闯不过
就回家啦,家是最温暖的!”自此陈玉展与太太并肩作 战,一起挑起传承社尾古早老味道的责任。他极为赞
赏太太的烹饪天赋,凡是她品尝过的食物,她都能无 师自通地调出相似的味道,这也让他母亲的厨艺得到 完美的传承。

下图|排屋式饭档店面宽敞,对 面就是七条路巴刹,无论客源 或采购都利便。
 38, Lebuh Cecil,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38, Lebuh Cecil,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分类、清洗是日常
陈亿光出生蔬菜世家,至今的人生都在新四合度过。
那时从菜农运过来的蔬菜,大的小的、好的坏的,表面

连着泥土几十公斤一并到批发商那里,他们还需分 类、清洗才能分销给小贩。15岁的陈亿光便是从这些 基本功练起,一步步做到现在坐在收银台。
那时,店面里24小时都有人工作,每天早上3点

到晚上8点则是门市时间,菜贩、餐厅、小贩或是零售 过来采购。在旧社尾,新四合除了柴埕前的店屋,在巴 刹里也有摊位。巴刹里,他们摊位的前方就是食肆。陈 亿光回忆当时的食肆,24小时都十分热闹,每天形形 色色的人经过:白天有上班族、凌晨则有夜猫子出没, 还有半夜在迪斯科狂欢后的时髦男女。
左图|新四合负责人陈亿光对旧 社尾的点滴一辈子不忘。
右图|由于蔬菜批发量庞大,新 四合需购下好几个摊格才足以 摆放每天的货量。
新四合
12 13 故事
118, Kompleks Pulau Mutiara, Gat Lebuh Macallum,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老翁茶
骑着单车叫卖送货
陈世烈18岁从中国南来,原来售卖水果,但水果
易坏,便转卖茶叶。创业初期,他一个人骑着单车到处
叫卖送货,辛勤十多年后才在社尾柴埕前和柴埕后租 下店面创立茶行,再买下店面。相较其他社尾老店,老
翁茶更早搬离社尾。2000年,政府的拆迁决定已经势 不可挡,于是老翁茶搬到柑仔园现址。
陈亚城的父亲陈世烈于1929年创立陈烈盛茶行,从中 国进口以乌龙茶为主的茶叶,再销至全马各地,既零

灯。凌晨三四点,蔬菜批发商的蔬菜便会铺满五脚基,
菜贩过来交易,到早上七八点店主们开门时就收摊。
70年代的晚上,陈家关店前会在五脚基留一盏

售也分销给杂货店和咖啡店做拉茶。茶行还有另一个 广为人知的名字——老翁茶。1970年代是老翁茶的鼎 盛时期,那时泰国和中国邦交关系未成立,不能直接

进口茶叶,因此马来西亚便成了中转站。老翁茶则是 槟城唯一一家出口中国茶叶至泰国的茶行。当时茶行 里工作的人有二十人之多,一天能包装上千包茶叶。
往事只能回味,他并没去过翻新后的社尾公园。他轻 描淡写地说,对于年轻人,是个新鲜好玩的去处;但对 他这样的老人来说,没什么意思啦。 茶行巅峰时期有二
517, Jalan Dato Keramat, 1046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十多工人,一天能 包装上千包茶叶。
老翁茶茶行老板陈亚城。
购买椰肉自行提炼食油
50年代起,王永榉开始在社尾做起杂货饲料、食 油批发生意。起初,他从当时还是一片椰林的日落洞
大路后购买椰肉自行提炼食油。生意越做越大,还一
度买下椰园。后来,他也开始售卖棕油、引进其他工厂 的成品代销。
王永榉的侄子王德忠在泉隆工作33年,从小受 大伯影响,培养出凡事要亲力亲为、尽力而为的人生 态度。他记得,店里最高峰时有十几位工人,主要工作 是包装、运送、记单等,大家的午饭都是店里特别准备 的员工餐。
王德忠与王慧诗Teresa(王永榉外孙女)不约而
同表示,老人家很节俭、对儿女也严格,生活朴实勤
奋,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天天去看铺。但另一方面,他也 大方资助有需求的亲戚朋友、提拔年轻人,还在中国 家乡南安出资建校。
8-10, Lorong Sungai Pinang, 11600 Jelutong, Penang Malaysia.


2012年之前,泉隆父子有限公司还在柴埕前,和社尾
万山旧址两相望,那是一间卖食油的老店。2012年,老 店搬到双溪槟榔继续营业,至今已传了三代人。这店
50年代开始在社尾扎根,泉隆的创办人王永榉过世多
年,后代们对于王老先生的创业过程和在社尾卖油的 经历仍记忆犹新。
王永榉的媳妇黄素凌还记得,家翁二十多岁只身 从福建南安来到霹雳江沙闯荡,后来辗转到槟城做生
意。或许是为人老实勤奋,这位年轻人获得万兴利老板 叶祖意的信任,让资本薄弱的他借贷赊账,最后以家禽 饲料、食油杂货白手起家。
泉隆父子有限公司创办人王 永榉,以家禽饲料、食油杂货 白手起家,是社尾街坊熟悉 的商家。
王永榉的媳妇黄素凌(中)、 侄子王德忠以及外孙女王慧 诗。王家对王永榉白手起家的 历程深感敬佩。
泉隆父子有限公司 14 15 故事

一景包点
(左起)郭慧卿、郭启明和郭 启强三姐弟坚守老字号,延续 着街坊对社尾一景的感情。
118,
Kompleks Pulau Mutiara, Gat Lebuh Macallum,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恋念老社尾
社尾拆迁是乔治市的重大事件,每隔一段时 间就会有相关报导。那几年,郭启明将报纸上有关 社尾万山的新闻搜集下来,集合成了一本厚厚的 剪报本子,想把这些报导留给孙子们看。毕竟,孙 子们还没来得及认识社尾万山,它便已走入历史。
左上图|郭启明的剪报本子和一景包点的绝版牛皮纸袋,几年 前已停用。那是一景包点最经典传统的包装。
左下图|三姐弟一起制作包点,三人精神体态皆优,让街坊们 天天有一景包子解馋。
右下图|走访许多社尾街坊,一说到社尾美食,他们一定会提 起“一景包点”,可见一景味道之深入民心。


一景包点1954年开始在社尾万山的食肆内营业,

专售广式手工包点。叉烧包、猪肉包、大包、玉米 包……个个馅料饱满,从揉面到包馅,都是当天完
成,新鲜热辣。
提到一景包点,许多老乔治市人还会想起郭
父的炒河粉。常常听上一辈的广府人感叹,如今的 炒河粉大多是预先炒好再放到锅里翻热,已经很
难尝到这种一盘盘现炒现卖的火候了。2004年底
搬出社尾万山后,一景包点也停售炒河粉了。
一景包点目前传到第二代,由郭慧卿、郭启明
和郭启强三姐弟合力经营。郭家三姐弟虽已年过 花甲,说起话来还是中气十足。
生机勃勃的市场
郭慧卿说起老社尾的兴旺场景,形容那时生
意可谓多到“钞票洒满地”。社尾万山食肆一个月
总会有一两次打斗。食客吃着吃着就和隔壁桌的 人吵起来,一手拿起玻璃汽水瓶便开打。他们早就 见怪不怪,在这些人打到档口之前,把碗碟、瓶罐 等易碎品收起来就好。“汽水瓶交给商家回收,下
次买的时候便有回扣。摔碎了多可惜!”
14 15 故事
16 17
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社尾
社 尾万山里的档主商贩,多为
人,社尾记载了他们的人生,他们
同样也见证了社尾的兴盛与没落。
曾经居住在此的他们,即使离开仍

心系社尾,一说起社尾就对从前往

事如数家珍。听着他们的故事,仿
佛也瞬间回到了那个热闹奔腾的
时代。
如今随着时代的进步,倒 夜香这行业已被抽水马桶 取代,那让人避之不及的 气味,也随着 社尾的旧时光 一同远去。
新四合
在倒夜香行业还在操作的年代,那气味对于陈
春好来说实在难以忘怀,她直呼:“那个粪桶真的很 可怕!请不要让我回到那个时代!”而如今随着时代 的进步,倒夜香这行业已被抽水马桶取代,那让人避 之不及的气味,也随着社尾的旧时光一同远去。
我的童年在这里
春天制作及艺术教室创办人陈春好,家族是经
营了近70年的蔬菜批发商“新四合”,自从社尾搬迁 后,新四合就搬入珍珠大厦。作为蔬菜批发世家出身
的孩子,她自嘲不太懂得区分蔬菜的种类。假期时,
婶婶曾找她来负责处理蔬菜的账务,不谙此道的她 却把账弄得一团糟,让大家啼笑皆非。

除了蔬菜,陈春好家族的商店还有出售鲜花,有 时会有基督教徒来光顾,她们会用盆子来摆设这些
花。那时候家中的孙女们都被家人派去大马路边排 排站,一人捧着一盆鲜花努力叫卖,两到三个小时即
可卖出百多盆鲜花,这也是她小时候特别有成就感 的事。在一天营业结束后,公公会把现钞取出,然后
大家围着一起数钞票。
对她而言,社尾最让她难忘的是浓浓人情味,街
坊邻里就像一个大家庭。然而不擅长记人名和人脸
的她,每每在街上听到熟悉的称呼不绝于耳:“阿好!
阿好!”她都会一脸茫然,直到对方自报家门,一段久
别重逢的对谈才能顺利开启。
不过陈春好坦言那里也是个龙蛇混集的地方,
除了有卖东西的商贩,其实有许多黑社会背景的人
士在那一带驻留,用她的话说:“黄赌黑都在这里”, 品流复杂的程度可见一斑。
18 19 故事
爸爸一直告诉我们,社尾总有
一天会结束。我家成为一个聚 集地,买卖虽然重要,但这里 更像是大家联络感情的地方。
源荣兴
透过那扇窗,看尽繁华兴衰
这些年,她透过那扇窗见过社尾最旺盛的 时期,却也看着社尾慢慢凋零。
“爸爸一直告诉我们,社尾总有一天会结 束。”超级市场的出现,一站式的购物服务,也让 社尾批发市场备受威胁。纵使做好心理准备,但 还是没人预期有天真的要离开这里。玉芝表示 父亲最舍不得的,是那班陪他工作几十年的工 人,“我家成为一个聚集地,买卖虽然重要,但这 里更像是大家联络感情的地方。”
后来源荣兴随着父亲的逝世就此停业。父
亲高流芳生前是槟城著名摄影师,高家三姐妹 选择在源荣兴举办摄影展,将父亲的摄影作品
一一展出,为父亲和源荣兴,划下完美的句点。
“源荣兴”是父亲的家族生意,也是高玉芝
从小住到大的地方,楼下经营米糖面粉批发和

零售,楼上就是他们的安乐窝。玉芝说,她最喜
欢她房间窗外的风景。一打开窗往下望就是社 尾热闹的街景,有商贩摊主来来往往的身影,也
曾见识过黑社会互拼打架的场面。 窗外的社尾,可以说从来不曾安静过。早上
的巴刹,下午和晚上的食肆,凌晨前来拿货的罗 里和货车,日复一日,她也早已习惯。后来到吉
隆坡升学,住宿的房间格外安静,没有了家乡熟
悉的嘈杂声,反而让她安静得想哭。对她而言, 那些声响代表着乔治市生活的动力,是社尾人 努力生存的迹象。
(左起)高家三姐妹高清玉,高玉
芝与高玉菁以及母亲(左二)在旧 店前合影,当年的源荣兴已变成榴 梿店铺(已关闭)。
我们每天就是进货、排货、搬 货、卖货、送货,一整天不停
进出摊格。所以你说,这么辛 苦的工作,有谁要做?
淇仁号
难聘请工人,曾经有个工人前来试工一天,就吓得不来工
作了。
用阿发的话说,平均每三分钟就有一个客人,所以

他们做事要很快,可以说是从早上8点开店忙到凌晨12
点多才关店。“有时忙起来,我吃了早餐就一直忙到傍晚 六点,忙到不会饿,就这样身体开始出状况。”
别看他们只是卖干货,背后的辛苦却鲜为人知,尤
其遇上雨季更麻烦。在运送过程遭受雨淋而变质的洋葱,
他们必须赶快散开所有洋葱,亲手处理发臭的洋葱。因为
工作搞得满身臭味,他在送货时会尽量避免和其他人一 起搭电梯,“所以你说,这么辛苦的工作,有谁要做?”
当初新巴刹风波一事,阿发也勇于发声,与其他街
坊力战到底,直到社尾巴刹被拆除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卖
货给上门的客人,“因为货真的太多了,只能边卖边搬,那 时我用了8辆罗里才能把所有的货载走。”
60、70年代,社尾巴刹是当时槟城最大型的批发市
场,单是卖干货的批发商行就有二十多家,淇仁号就是其 中一家,专门批发洋葱、蒜头、香料与酱料等干货。在社尾
巴刹寿终正寝后,淇仁号就入驻五条路珍珠大厦。
人称“阿发”的杨宝发是淇仁号第三代传人,由公公
创立至今已超过80年历史。淇仁号本来由杨宝发三兄弟
合力经营,不过后来因健康问题,目前已全权交给哥哥杨 宝福打理。
那时不足150坪的摊格,挤满一箱箱干货,他们习惯
将干货层层叠高,甚至叠到天花板,在关店以前,这些层
层叠叠的货物一定会在当天卖完。“我们每天就是进货、 排货、搬货、卖货、送货,一整天不停进出摊格。”由于人手
不足,他们几乎一人做三人份的工作,超高工作量导致更 昼夜交接,忙不停歇
20 21 故事
在社尾生活的日子,李永 明常记录社尾万山的盛 况,成为画中风景。
画家

社尾的李老师
54岁槟城水彩画家李永明,小时候居住乔治市 十七层组屋。十七层距离社尾只有几步路之遥,跟着
父亲逛巴刹、吃福建面、以及巴刹鸡肉档的腥臭味,是
他小时候对社尾的印象。
中五毕业后,才20岁的他就此展开教画生涯,教
过的学生不计其数。在长达30年的教学生涯中,李永
明曾经在社尾待过5至6年光景。那时为了教学方便,
他租下义隆米店楼上三楼作为“永明绘画中心”。
李永明擅长人物创作,社尾巴刹里劳动的人们,
此起彼落的说话声、叫嚷声,都成了他作画的灵感。在 绘画教室开窗往下望,巴刹的热闹景况尽收眼底。他

喜欢观察社尾的每个人,那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
般邻里人情味,尤其让他深深着迷。
曾经,社尾时不时听闻命案的发生,有一宗个案
让李永明特别印象深刻。“那时有命案发生在一个饭 档前面,后来警方捉到凶手,他也叫李永明啊!竟然跟
我同名同姓,因为我在那边教画,大家都认识我,街坊 就一直拿这件事开玩笑。”
那段教学的时光,他几乎从早上待到傍晚,三餐
都在当地解决。随着慢慢融入社尾生活,与社尾人熟
识,让他至今对社尾依然有一份牵挂。
“只有在那边待过的人,才能够了解社尾的魅 力。”李永明说。
22 23 故事
只有在那边待过 的人,才能够了 解社尾的魅力。

在一个有在地刊物 的地方过日子吧!
作为一个从2000年开始从事杂志工作的“老 杂志人”,我心目中理想的生活与杂志工作是这样 的:办一本真正的接地气的中国地方杂志,每一期 杂志花费三年时间,选择一个较为少人关注的城 市(人口规模在50万-200万)——比如是天水、榆 林、诸暨、武夷山、齐齐哈尔、漳州、浮梁、余杭、临 海等。
我们的编辑们在这些城市定居三年,从生活 体验到文化考察,以国际眼光和成熟的现代杂志 操作方式来呈现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主旨是接 地气、生动、彻底陌生又切中要害的真实。以前这 样的考察叫作“地方志”,但我们可以把它变成真 正的“杂志”。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杂志工作方式。
大城市X小地方各司其职
在我作为编辑顾问的最新一期《乐活 LOHAS》杂志中,我发起倡议:在未来,更可持续的 生活方式,一半在大城,一半在小地方。大城负责 喧嚣,负责以一种“作”的舞台方式进行生活,负责 认识陌生人,负责体会全球化品质生活的美好;小 地方负责静谧,负责一种“真我”的自然状态进行 生活,负责和睦亲近,负责回到原生土地的去标签 化的真实。
的确,这些年,在地创生,在地创作,是热话。 越来越多的机场和高铁线直达小地方——比如在 浙江、福建,几乎每个县市都通了高铁。从大城市 发起一个说走就走的小旅行,从城市CBD溜达到 一个无人认识你的小村落,也就2-3个小时的功
30 31 观 察
“小城X计划”在地刊物活动外场,活动评价高,因 反应积极而展览加日。



夫。你付出一点点“城市离线”的代价,换来的却是 一整个小地方的滋养。你所看到的世界,既陌生又 有一种文化血脉里的相近。
我在帮日本的地方创生促进组织D& Department Project的杂志《d travel》做其中文 版《d设计之旅》时,便意识到这种地方原生的力 量——这个团队从2000年开始,以每年做2-3册的 速度,要把日本47个都道府县(相当于中国的省 份)各做一册杂志,报道每个地区的地方风物和设 计力量。也借由长冈贤明以及他的团队的努力,地 方的力量在日本这样高度发展的设计国度,依然保 有重要的意义,拥有地方设计特色的地方更是充满 魅力。正所谓:越在地,越美丽。
本地人做地方志
琳琅满目的在地刊物,让展场回荡着精彩的地方声 音。

中国疆域接近是日本的25倍,也就说如果我 们要做这样的杂志,可能以D & Department的方 式做起来要花费百年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仰仗 每个地方的觉醒,每个地方的人们自己来做一本属 于自己的地方刊物,它既有地方的乡音,又可以与 相邻地域形成同样的频道。
在浙江的小城临海,五月文创正是一个这样 的有趣团体,这些选择扎根地方,在地创生的年轻 人,发起了一个在地创造社群。今年五月举行的“小 城X计划”已经走入第三期,以“在地”为议题通过 展览、分享会、放映等进行不同方面的呈现。这次举 办的“在地刊物展”,搜罗了120多种地方刊物,以 整体呈现的面相展现近年来在中国、乃至亚洲的优 质地方杂志和出版物。我由衷地觉得,在地刊物,它 才方兴未艾。
让我们一起,在一个有在地刊物的地方过日 子吧!
来自中港台,澳门,大马及日本的在地刊物同聚一 室,让读者们徘徊久久不去。
Penang at a Glance is a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captured from the lenses of four local photographers coming from four different backgrounds. The book showcases Penang’s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festivals, celebrations, arts, culture, heritage, people and lifestyles.







Available to purchase in stores and online at www.georgetownfestival.com




Tanjong Life: The New Norm is a comic book illustrated by Penang-born cartoonist Azmi Hussin. Follow the funny adventures of Joe G – Azmi’s buck-toothed, true-blue Penangite character – as he explores the amusing and the not-so-amusing sides of the new normal in Penang!

34 35 观 察
disposed face masks can do, Joe G has undoubtedly found the lighter sides of the new normal to keep us going.
ISBN 978-967-19182-1-0 978967191821 0
www.georgetownfestival.com
to purchase in stores and online at www.georgetownfestival.com
Available
画家| 张桂佩
本地建筑师,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 建筑系。擅长水墨画。
年份| 2020年
媒介|
墨、消毒液、宣纸
尺寸| 150cm x 100cm

《彼岸花》是张桂佩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创作的作品。她从显微镜下病毒的形貌获得灵 感,将这些天天必备的消毒液和墨泼到镜子上,再铺上宣纸将这两种物质碰撞的瞬间定格 下来,象征无处不在的病毒。
瘟疫与死亡,总是令她想起传说中的彼岸花。相传彼岸花长在忘川河畔,引领生魂走向 幽冥地狱。生魂渡河而忘前生,前生记忆则化作彼岸花。创作者让两朵小花盛开在纷乱之 中。死亡以后,曾经的回忆不会化为乌有,而会在某处继续盛开。
我们终将化作混沌中的彼岸花,不知来路,不问去路,但仍不忘绽放,在无尽的混沌中留 下印记。
文字 | 张桂佩、赵慈宇
《彼岸花》
34 赏 画

LEFT |
As part of an art installation, vegetables and fruits were placed along the walkway to the market. Volunteers wearing boots would mimic the hawkers by tossing the vegetables and fruits into the water with a shout “Sia Boey!”. It was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installations of the exhibition.

The “Farewell, Sia Boey” exhibition brought together many local artists to present a multifaceted portrait of Sia Boey.
artists Text by Translate by
RIGHT |
Documenting an era through
Khoo Cheang Jin and Ch’ng Kiah Kiean, and a USM student
–
In 2001, the Nanyang Folk Culture Society organised an art exhibition titled “Farewell, Sia Boey” to commemorate the Sia Boey wholesale market which was soon to be relocated. The society gathered a group of arts and cultural workers to capture their impressions

love of historical sites, culture and arts. This exhibition also brought together three other Penang residents
from Johor Tang Kah Teng –who, 21 years later, returned to a completely redeveloped Sia Boey to reminisce about the exhibition at the chaotic but vibrant marketplace that once dominated the area.

of the much-loved landmark through art. Initially, this group was made up of Penangites who had returned from their studies in Taiwan, such as Sachi Choo, Tan Yeow Wooi, and Ooi Bok Kim. All of them shared a

|
|
LEFT
There was a bulletin board at the art exhibition detailing the history of Sia Boey. RIGHT
Other than live sketching by Khoo Cheang Jin, there was also a drawing contest for children.
See Chiew Yen Catherine Fong Life 36 37
(Photo credit by Khoo Cheang Jin and Tan Yeow Wooi)



“We, the ones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this, hoped to use a costefficient way to document an era.”
TANG KHOO CH’NG
Live sketches and art exhibition
At the “Farewell, Sia Boey” art exhibition in 2001, Khoo Cheang Jin was tasked to do live sketching on-site. There was also a drawing contest for children as well as art installations and performances by various artists. Volunteers had selected the vacant hawker stall lots and empty aisles to exhibit the paintings.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still a handful of stall owners who continue to operate as though in an expression of futile resistance before Sia Boey market was history. Ch’ng Kiah Kiean mentioned that there was a rather special performance where vegetables and fruits were placed along the sidewalk next to the canal and the artists would toss the vegetables and fruits into the canal while yelling “Sia Boey!”, mimicking the hawkers who would often dump leftovers into the canal. It was just like what Khoo Cheang Jin said, “We, the ones who are passionate about this, hoped to use a cost-efficient way to document an era.” Johor native Tang Kah Teng participated in the “Farewell, Sia Boey” event while still a student at USM. In the days leading up to Sia Boey’s relocation, she came across numerous reports in the local press about the conflicts and disputes related to the move, and was intrigued by the deep affection Penangites had for a local market. It was something she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So, she decided to visit Sia Boey market to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herself. From the hawkers, she learned that they were reluctant to mov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felt helpless at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 relocation. “I realised then that Sia Boey market was not just a market. It was more like a closeknit community that brought all the people in the neighbourhood together. No other market I know had such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enang’s history.” After graduating, Tang Kah Teng decided to stay on in Penang. She did not deny that her experience at Sia Boey so long ago had persuaded her to settle down in Penang.
Tang Kah Teng , who hails from Johor, participated in the “Farewell, Sia Boey” exhibition as a student volunteer from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The event made such a deep impression on her that it became one of the reasons she stayed on in Penang after graduation.
Khoo Cheang Jin is the president of Penang Watercolour Society and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international watercolour artists’ circle. Before Sia Boey market was relocated, he would sketch the scenery alone or with a like-minded friend who loved to draw at the area. To him, Sia Boey is a great subject. He said with a smile: “Although the place was very dirty, noisy, and the drains were smelly, it was very vibrant and lively –a worthy subject for a painting.”
Ch’ng Kiah Kiean is best known for his beautiful sketches of Penang. Streetscapes are his favoured subject. As a resident of Lebuh Melayu, he shops and dines at Sia Boey regularly. “Since young, I always felt that Penang is a most beautiful place. I have documented Sia Boey through different eras.”
Life 38 39
Music


as a voice –it can be both a nostalgic memory and a silent protest. Two children who grew up together at old Sia Boey parted ways when their families moved away. They lost touch for decades but because of music were reunited. Their love and memories of Sia Boey were immortalised in a song titled “Old House with Red Roof Tiles”. Another song, “Song of the Street”, was their own rendition of a well-known nursery rhyme. It was dedicated to all who missed Sia Boey.
改编&演唱 :汪荣木 柴埕后出名是红公间红公间对面是人车间
Translate by Catherine Fong Photos by Tan Yeow Wooi
Text by See Chiew Yen


行伫坡底的港仔墘,想起细汉彼当时,逗阵作伙的老厝边,毋知搬到叨位去。看到古早的红厝瓦,父母艰苦去趁食,为著生活出外底打拼,离开老厝的我转来行。

改编&演唱 :汪荣木

街路边的歌
人车间人车真多出出入入真无闲(繁忙)哎呦欸哎哟欸哎哎呦
柴埕后出名是红公间红公间对面是人车间 人车间人车真多出出入入真无闲(繁忙)哎呦欸哎哟欸哎哎呦哎呦欸哎哟欸哎哎呦
红厝瓦的老厝 词 : 乙狼 曲 : 郭芝玲 行伫坡底的港仔墘,想起细汉彼当时,逗阵作伙的老厝边,毋知搬到叨位去。看到古早的红厝瓦,父母艰苦去趁食,为著生活出外底打拼,离开老厝的我转来行。 红厝瓦的老厝,有咱过去的故事,红厝瓦的老厝,有咱温暖的情分,来转去看咱的,破旧的老厝。





为著生活出外底打拼,离开老厝的我转来行。
Life 40 41
Drying salted fishin the sun is a common scene at Sia Boey.
(Photos by Tan Yeow Wo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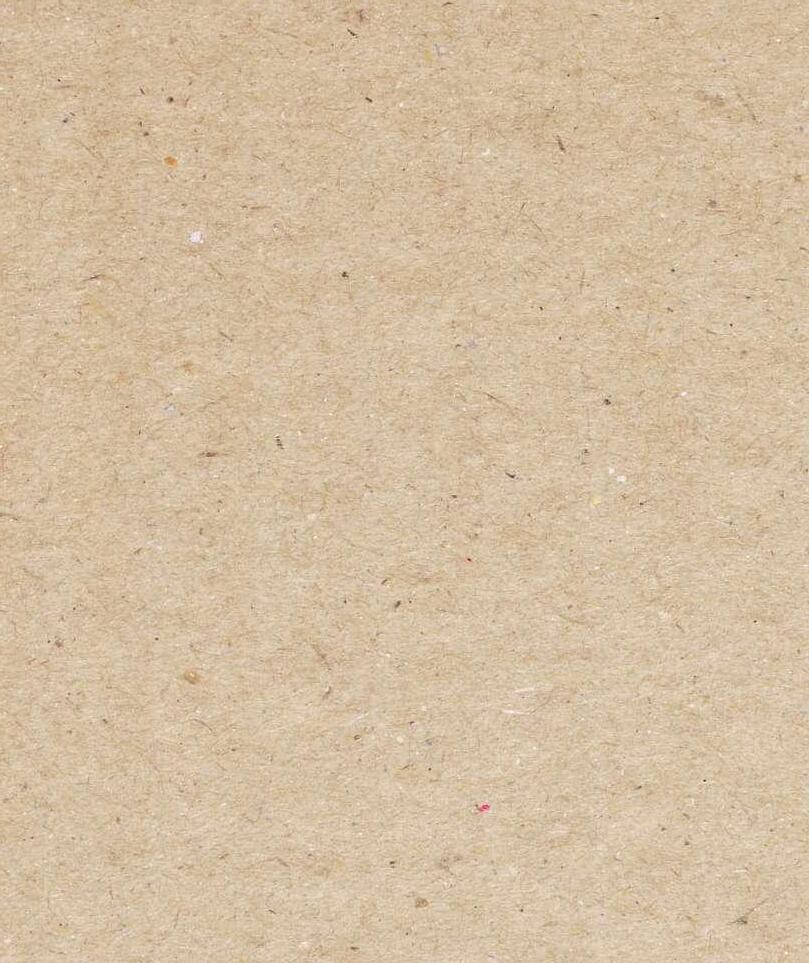




Sun-drying salted fish at the playground


Three generations of local music producer Ang Eng Bok’s family lived at Sia Boey. He was also Tan Kok Keong’s childhood friend. Tan was a little older and was regarded as the “big brother” among their playmates. They got to know each other while playing badminton. Back then, there were no badminton courts in the neighbourhood. Instead, the boys would draw a few lines on the road and made the road their badminton court. At that time, there was a playground behind Sia Boey market. Ocassionally, some adults would use the playground to dry their salted fish, and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would mingle. “The adults did their work while the children played,” Tan said. Rearing pigeons and fighting fish was a trend back then. When pigeons were no longer popular, fighting fish became the main pursuit. People would rear fighting fish at Ang house and hold fighting fish contests there too.
Previously, there was an eye-catching “golden door” at one of the 22 houses in Sia Boey. The goldpainted wooden door gleamed in the sun. This was Tan Kok Keong’s house on Jalan Maxwell. He was a part-time writer and songwriter who had a flair for writing Hokkien song lyrics. In his house, ten family members would squeeze in together and sleep sideby-side. An old fan would make a mechanical “kala-

Ang Eng Bok (left) and Tan Kok Keong remember Sia Boey

Childhood friends
Penang-themed music album





In 2014, Ang Eng Bok had an idea to compile a collection of Penang-themed Chinese, Cantonese, English, Malay, and Tamil songs call “Oh! My Penang”. He invited nine music producers from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to write a song each about Penang. One of them was Tan Kok Keong. His masterpiece “Old House with Red Roof Tiles” was a tribute the old Sia Boey. Coincidentally, the composer of the song, Koay Chee Lin, was also a resident of Sia Boey. Ang has written songs about other places in Penang too. “Song of the Streets” is about Lebuh Bakau in the 1980s. In the lyrics, the “red house” (temple), “workshop” (rickshaw shop), “noddle shop” (noodle-making shop) and opium shop were references to places locals would be familiar with. It was originally sung at Lebuh Bakau in the 1980s. Ang had recomposed the song based on his memories of the place.
The red house at Lebuh Tek Soon
The “red house” at Lebuh Tek Soon was Ang Eng Bok’s house. Whenever the community celebrated a deity’s birthday, a stage would be set up next to his house with electricity supplied from his house. Stage performers –which included local singers such as Kang Qiao and Elaine Kang –would also come in for a rest or toilet break in his house.
<<Oh! My Penang>> that centred on Penang had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Cantonese, English, Malay and Tamil songs.
Ang’s uncle was the stage manager and would store musical instruments such as stereos and drums in their home, which Ang would play with secretly. Perhaps it was because of this early exposure to musical instruments that Ang, who admitted to singing poorly since young, chose instead to be a music producer.
Life 42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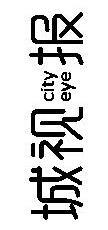





















 38, Lebuh Cecil,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
38, Lebuh Cecil, 10300 George Town, Pulau Pin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