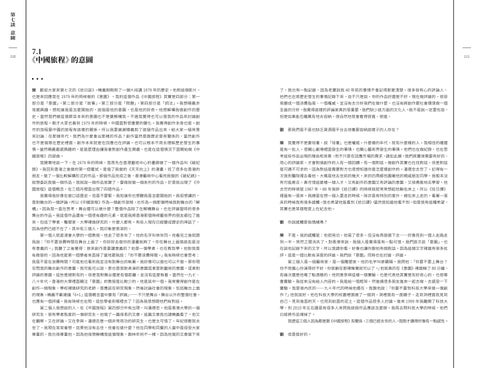第七談 意圖 110
7.1
《中國旅程》的意圖
111
···
榮 歡迎大家來第七次的《拾日談》。曉義剛剛剪了一個片段講 1979 年的歷史。他剪這個影片,
了,我也有一點記錄,因為老實說我 40 年前的事情不會記得那麼清楚。很多很有心的評論人,
部分是「意圖」,第二部分是「故事」,第三部分是「問題」,第四部分是「詞法」。我想曉義非
易變成一個消費指南、一個權威,並沒有去分析我們在做什麼,也沒有將創作跟社會環境做一個
也是來回應我在 1979 年的時候做的《意圖》。我的這個作品《中國旅程》其實是四部分:第一
常感興趣,想知道我是怎麼開始的,這個是他的意圖,也是他的好奇。他想解構我做創作的歷
史。當然我們做這個節目本來的意圖也不是要解構我。不過我覺得也可以借我的作品來討論創 作的旅程。剛才大家也看到 1979 年的時候,中國面對很重要的變化。我覺得創作本身也是。創
他們也在將歷史發生的事情記錄下來,並不只是說,你的作品好還是不好。現在做評論的,很容
全面的分析。我覺得這樣的評論家真的很重要,我們缺少這方面的文化人。我不是說一定要包容, 但是如果能包羅萬有地去容納,很自然地就會看得很寬、很遠。
作的旅程跟中國的旅程有這樣的關係。所以我要謝謝曉義剪了這個作品出來,給大家一個背景
劉
也不是侷限在歷史裡面,創作本來就是在回應也在評論,也可以根本不用去理睬歷史發生的事
榮 我覺得不是要培養,說「培養」也是權威。什麼樣的年代,就有什麼樣的人。我相信的確還
國旅程》四部曲。
考這些作品出現的理由和背景,而不只是在回應市場的需求,諸如此類。我們其實很需要有好的、
來討論:在那個年代,我們為什麼會出那樣的作品?創作當然是跟歷史是有關係的,當然創作 情。當然曉義最感興趣的,是甚麼理由讓我會對創作產生興趣,也是在這個情況下面開始做《中
我簡單地談一下,在 1979 年的時候,我首先在香港藝術中心的畫廊做了一個作品叫《破紀 錄》。我回到香港之後做的第一個嘗試,是借了我做的《天天向上》的漫畫,找了很多在香港的
朋友,做了一個比較解構形式的作品。那個作品完成之後,香港藝術中心看完我做的《破紀錄》, 就想委託我做一個作品。我就說一個作品就算了,要做就做一個系列的作品。於是就出現了《中 國旅程》這個概念,在三個月裡面出現了四個作品。
我覺得我好像在做口述歷史。但是不要緊,我知道你也想聽我是怎麼開始的。我很想講的, 是對舞台的一個評論。所以《中國旅程》作為一個創作旅程,也作為一個那個時候我對舞台的「解
構」。因為我一直在思考,舞台還可以做什麼?整個作品除了在解構舞台,也在評論當時的很多
舞台的作品。我這個作品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元素,就是我將香港那個時候藝術界的朋友都拉了進
那我們是不是也缺乏資源跟平台去培養跟容納這樣子的人存在?
是有一批人,很關心劇場裡面發生的事情,也關心藝術界發生的事情。他們也在做紀錄,也在思
用心的評論家,才會對搞創作的人有一個回饋,有一個對話。做創作其實也在找對話,但是對話
是可遇不可求的,因為對話是需要對方也很想知道你是怎麼樣創作的。潘德忠去世了。記得有一 次我到醫院裡去看他,大概是他去世前的幾天。床的四周都包圍著他的親戚朋友同學,我根本沒 有可能進去。真可惜這麼樣一個人才,又有創作的意圖又有評論的意圖,又很勇敢地去學習。他 去世的時候是 1987 年,88 年我排《拾日譚》的時候我就常常想起他躺在床上,所以《拾日譚》
裡面有一張床。我總是在想一個人要走的時候,除非是有特別的意外,總在床上走的。看著一張
床的時候我有很多感觸。我也希望他能看到《拾日譚》 ,當然我知道他看不到,但是我有這種希望, 其實也是某個程度上在紀念他。
來,包括了學者、雕塑家、大學裡做研究的,什麼人都有。有些人現在已經變成歷史的神話了,
劉 你說感觸是指情緒嗎?
第一個人就是浸會大學的一個教授,他走了很多年了,他的名字叫林年同。他看完之後就跟
榮 不是。我的感觸是:他很用功,他寫了很多,但沒有再發展下去——好像見到一個人走路走
有意義的。」我聽了之後覺得:原來創作是要講意義的?他是一個學者,也在教哲學。他對我是
在談他記錄下來的文字,所以我請你看,好像也讓你跟他有個對話。因為這個文字裡面有很多批
因為他們已經不在了。其中有三個人,我印象是很深的。
我說:「你不要浪費時間在舞台上面了,你好好去做你的漫畫就夠了,你在舞台上面搞這些是沒
有啟發的,因為他是第一個學者來直接了當地跟我說:「你不要浪費時間。」我有時候也會思考:
我是不是在浪費時間?可能他也看到我並沒有對舞台的執著,我好像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你現 在問我的舞台創作的意圖,我可能可以說,那也是我對表演的意圖或者是對藝術的意圖,或者對
評論的意圖,這些是絕對有的。但是我對舞台還是有個距離,並沒有這麼執著。當然在一九七、 八十年代,香港的大學裡面關注「意圖」的教授是比較少的,他是其中一個。我常覺得創作是在
創作一個現象,學校裡做研究的老師,是應該在研究現象,然後討論社會的現象,包括舞台上面
的現象。曉義不斷建議「6+1」這個概念當中要有「評論」——不只是舞台,舞台以外的整個社會, 也應有一個評議。我有時候也在問,這些學者到哪裡去了?因為我很想跟他們有對話。
第二個人我想談的人,在《中國旅程》第四部分中有出現,叫潘德忠。他是香港大學的一個
研究生,很有學者態度的一個研究生。他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這篇文章我也請曉義看了。他又 在觀察,又在評論,又在參與。潘德忠是一個非常用功的研究生,也是太可惜了,年紀很輕就去
世了。我現在常常會想,如果他沒有去世,他會在做什麼?他在同學和同輩的人當中是很受大家 尊重的,我也很尊重他。因為他很想解構我這個現象,跟林年同不一樣。因為他寫的文章留下來
到一半,突然之間消失了。對香港來說,我個人是覺得是有一點可惜。我們這次談「意圖」,也 評,這是一個比較有深度的評論。我們談「意圖」同時也在討論、評論。
第三個人是一個藝術家,是一個雕塑家。他的名字叫麥顯陽。我問他:「你要不要上舞台?
你不用擔心你演得好不好,你就躺在那裡睡覺就可以了。」他就真的在《意圖》裡面睡了 80 分鐘, 有幾次還是他喝了點酒睡的。他同意參與這樣一個實驗,也是代表他其實是有好奇心的,也很尊 重實驗。我從來沒有給人內容的。我是給一個框架,然後請很多朋友進來一起去做,去感受一下 實驗。我是很內疚的——九十年代的時候他還在,我跟他說:「你要不要到科技大學來做一個創
作?」他就說好。他在科技大學的校園裡面做了一個洞,洞裡面有一面鏡子,走到洞裡面就見到
自己,見到後面的天,也見到前面的泥土。這個作品很多人討論。後來 1999 年我離開了科技大 學,到 2010 年左右還是有很多人來問我這個作品應該怎麼辦。我再去問科技大學的時候,他們 已經將作品埋掉了。
我提這三個人因為都是跟《中國旅程》有關係,三個已經去世的人。我剛才講得好像有一點感性。 劉 但是挺好的。